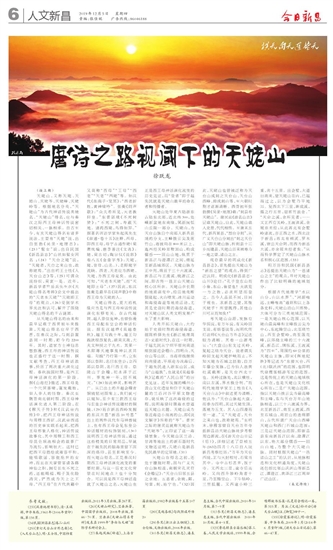(接上期)
天姥山,又称天姥、天姆山、天姥岑、天姥峰、天姥岭等。根据地名分类,“天姥山”为古代神话传说类地名。“天姥山”得名,应与秦汉之际西王母神话传说密切相关、一脉相承。自古至今,有关天姥山得名有诸多说法,主要有“天姥”说,出自张勃《吴录·地理志》;(23)“髽女”说,出自民国《新昌县志》“山状如髽女因名 ;(24) “天台之姥”说,“天姥者,天台之来山也,故称姥焉。”出自明王士性《入天台山志》等,(25)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新昌学者竺岳兵先生在《天姥山得名考辨》论文中提出的“天老本天姥”“天姥即王母”的观点,(26)受到学术界关注和认可,解开了围绕天姥山得名的千古谜团。
从天姥山得名的由来和最早记载于西晋初年来推算,天姥山得名应早于西晋,在秦汉之际,与剡县置县同一时期,距今约2200年。其时,道家方士神仙思想弥漫,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也正盛行于这一时期。据文献考查,西王母神话故事,经历了两次重大演化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西王母神话演化的第一阶段。据《山海经》描述,西王母是一个穴居善啸,蓬发戴胜,似人非人的怪物。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神话演化进入第二阶段,在《穆天子传》和《汉武帝内传》中,把西王母神话传说与周穆王西征、汉武帝西巡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把西王母形象人格化,神话传说故事化,其中周穆王和西王母昆仑瑶池相会的故事广为流传,影响很大。这时已把西王母描绘成雍容平和、能唱歌谣、容貌绝世的女神,而且在天掌管宴请各路神仙之职,拥有长生不死之药,还能赐福、赐子及化险消灾,俨然成为天上之王母。“西王母”在古代典籍中又简称“西母”“王母”“西老”“天老”“西姥”等。如汉代《淮南子·览冥》:“西老折胜,黄神啸吟”。张衡《同声歌》:“众夫希所见,天老教轩皇。”东晋郭璞《不死树赞》:“不死之树,寿蔽天地。请药西姥,乌得如羿。”据著名训诂学家朱起凤先生《辞通·卷十五》注释,西母,即西王母,母字古通作姥(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姥,莫古切;陶宗仪《说郛》卷八五《金壶字考》:天姥,姥,音母,山名。),老即姥字讹缺。西老、天老应为西姥、天姥,为西王母是矣。由此可知,“天老本天姥”,而“天姥即王母”。(27)因此,东汉张衡是最早在《同声歌》中称西王母为天姥的人。
天姥山得名,更大的机缘应当是与西王母神话传说演化东移有关。在古代越国,越人崇信鬼神,也曾弥漫西王母配东皇公的神话传说。据东汉越晔《吴越春秋》,越王勾践十年,越王勾践欲报怨复仇,破吴灭敌,大夫文种授之于九术。其第一术即尊天地事鬼神以求其福。勾践“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事鬼神一年,国不被灾。”(28)如此神灵,影响甚广。从已出土的古越会稽青铜镜铭刻图案上,我们就可以窥知,至少有三款西王母与东皇公神话传说题材的铜镜。(29)而在新昌西岭发掘的东汉古墓“新昌10号墓”出土的两件汉代车马神兽镜上,也有西王母会见东皇公神话题材的纹饰铭刻,(30)说明西王母神话传说,通过这些精美的日常用品,早就在于越先民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影响至今。而天姥山得名,正是秦汉时期西王母神话演化流变的重要时期,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在时间地点上也十分契合。可以说是西王母神话造就了天姥山之名,天姥山也正是西王母神话演化流变的历史见证,而“登者”即于越先民就是天姥山最早的命名者和传播者。
天姥山处华夏古陆浙东古陆东北部,近北纬300,处嵊新盆地东南缘,属浙闽低山丘陵一部分。天姥山,为天台山脉自中南部入新昌县境的分支,主峰拨云尖及班竹山,海拔均在800米以上,迤西经关岭至鞍顶山,构成儒岙——回山山地,纵贯于新昌江与澄潭江之间,绵延至新昌城郊区。天姥山脉为正中列,绵亘于三十六渡溪、新昌江与王渡溪、桃源江之间,即古传一邑主山天姥山核心区所在。天姥山在长期的地质演变中,经历地壳断裂隆起、火山喷发、冰川运动和海侵海退等地质活动,尤其是史前时期的海侵海退,对天姥山区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类开拓天姥山,大约始于史前时期的海侵海退。据陈桥驿先生《浙江地理简志·史前时代》,在这一时期,于越先民从宁绍平原向南退缩到接近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等山区。当海岸线继续向南侵进,平原沦为浅海后,于越先民进入浙东山区,成为“山越族”,也就是《吴越春秋》记载的“人民山居”的历史见证。近年发掘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和位于天姥山麓的兰沿河谷平原文物遗存,就反映了这次海侵的过程,说明海侵时期海水曾逼近天姥山北麓。天姥山成为靠近海边小而高的山,即《说文解字》所称的“岑”。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就称天姥山为“天姥岑”,正印证了这一海侵景象。今天姥山区兰沿、甘湾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还证明,天姥山是新昌先民最早的定居地。(31)
天姥山在得名之初,还处于朦胧时期,因与广义天台山脉相连,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天台山旧居五县之余地。五县者,余姚,鄞,句章,剡,始宁也。”(32)因此,天姥山也曾被泛称为天台山或剡之天台山、天台山西峰、抑或剡山等,至六朝时期才逐渐清晰。西晋初年张勃撰《吴录·地理》载:“剡县有天姥山”。谢灵运《游名山志》记载天姥山,自此,天姥山载入史册,代代相传。至唐末五代,新昌置县,“割台分剡”,从广义天台山分割出“剡之天台山”即天姥山脉,析剡县十三乡而建县,天姥山历来被尊为一地之望,诸山之主。
现存最早的明成化《新昌县志》,首先提出天姥山为“新昌之望”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明成化《新昌县志·山川》论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东山,鲁望也!夫欲览一方之胜,必求所望而登之。古今人品虽不同,目同于视也。求新昌之望,其惟天姥乎?所望既得,其他山川可从而知矣!”
考天姥山山源,发脉有华顶说,有万年说,有关岭回支说,有括苍说等,而明代传灯法师《天台山方外志》记述较为清晰。其卷一山源考云:“(大盘山)东支过关岭,复起之结为天台。说者谓关岭回支起天姥护峡而止,不知天姥为石城之胚胎,自万年藤公发脉,已为仙人浪黄杜溪截断,是天台西北干也。关岭过脉处,北以横杜,南以左溪,界水极分明。”而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入天台山志》中叙述更为清晰,他认为:“天台山脉起大盘,而委为四明,其过天姥发顶,落地为五支。其入山四漫而非一途。”又“天姥者,天台之来山也,故称姥焉。”至明末,徐霞客曾自天台万年寺抵新昌沿天姥山脉徒步考察周边源流,在《游天台山日记(后)》,详细记述了崇祯五年(1632)四月十八日自入境新昌考察经历:“万年为天台西境,正与天封相对,石梁当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饭于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后高岭。又向西升陟岭角者十里,乃至腾空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天台之溪,余所见者:……又正西有关岭、王渡诸溪,余屐亦未经;从此再北有会墅岭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于新昌;再北有福溪、罗木溪,皆出天台阴,而西为新昌大溪,亦余屐未经者矣。”从而科学界定了天姥山山脉水系和核心区范围。(33)
明万历和民国《新昌县志》还提出天姥山为“一邑诸山之主”的观点,并对天姥山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地域划分。
根据古代地理学“水以山分,山以水界”、“河源唯远,主峰唯高”通则和以上各条史料,天姥山的山川形势,大体可分为三类地域范围:一是天姥山核心范围,以天姥山最高峰和主峰拨云尖为中心,东起腾空山,北至班竹山,西至会墅岭,南至莲花峰,以环绕主峰的三十六渡溪、新昌江、惆怅溪、王渡溪为“四至”,周围约60公里的天姥山主脉,即宋《舆地纪胜》等记述为“东接天台,西(北)联沃洲”的范围,也即明代徐霞客栖游考定的范围。这是传统上的天姥山地域核心所在,也是天姥山文化核心所在;二是广天姥山范围,指以天姥山拨云尖为最高峰和主峰,东与天台万年山地脉相连,以三十六渡溪为界,北至新昌江,南至王渡溪,西至石城山、南岩山的连绵群山,古代所谓广天台山西峰天姥山和西门石城山范围;三是泛天姥山范围,即新昌县东南新昌江以南、澄潭江以东,绝大部分儒岙——回山山地,为整个大天姥山脉。同时根据天姥山“一邑诸山之主”的认识,从地脉相连和文化相通角度,天姥山还包括比邻山沃洲山等新昌江、潭澄江、黄泽江三江两岸广泛山区。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23)《汉唐地理书钞》,清·王谟辑,中华书局,1961年(2006年重印)版,第156页。
(24)民国《新昌县志》卷二·山川
(25)《重订天台山方外志要》之《入天台山志》,明·王士性,中国档案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第267页。
(26)《天姥山研究》,竺岳兵著,中国国学出版社, 2008年出版,第46-70页。竺岳兵《天姥山得名考辩》发表在1999年“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27)朱起凤编《辞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卷十五第107页
(28)《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20
(29)参见《浙江出土铜镜》,王士伦编,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
(30)参见《新昌文物志》,潘表惠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7-9页
(31)参见《新昌文物志》,潘表惠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年10月版,第4-5页。
(32)《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会稽郡故书丛集·孔灵符会稽记一卷,第315页。另注:《文选》孙兴公《游天台山赋》注。《御览》四十一。
(33)《徐霞客游记》,明·徐霞客著,中华书局,2009年1月(2014年6 月重印)版,《游天台山日记后》,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