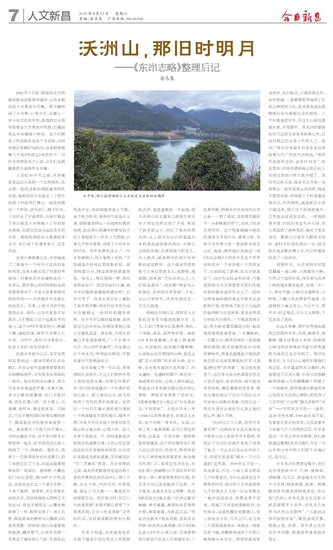俞志慧
1983年7月底,刚刚毕业的我接到新昌县教育局通知,让我去新昌县大市聚农中任教。那天辗转到了大市聚,已是中午,在镇上一家小吃店吃的中饭,热情的店主得知我要去大市聚农中任教,打趣说我去水帘庵做小和尚。这个时候我才听说新昌还有个水帘洞,当时电视正热播《西游记》,店家特别提醒可不是《西游记》里的那个。旧时水帘洞前有个小庙,乡民们也就随缘把小庙唤作水帘庵。
上世纪50年代之前,水帘庵还是远近乡民的一个信仰场所,在这里一起任过教的胡柏藩老师告诉我,他的奶奶早先还从二十里外的胡卜村赶来打佛七。庙里的最后一个和尚,法号济仁,精于针灸,土改时去了宁波劳改,在狱中教会了来自新昌大市聚姚卜丁村的狱友梁桢,后者出息成为远近有名的中医。梁桢医师的女儿梁德妃承父业,也已成了非遗传承人,这是后话。
出家人被驱离之后,水帘庵成了二里地外一个叫外大坑的村落的用房,后来大殿又成了村里的养猪场。村集体在水帘庵附近有一处茶山,看护茶山的村民相标也捎带着照看寺产,于是大家都管他叫相标和尚——虽然他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后来,上面号召把学校建到山区、海岛,山旮旯里也不甘落后,人们想起了这个远离市井的地方,遂于1975年轰走牲口,掀翻大殿,建起校室,唤作大市聚五七中学。1979年,改叫大市聚农中,社会上念旧,叫水帘农中。
我到水帘农中以后,在学校资料室看到过一部油印的《东岇志略》。在办公室外还能看到零星的石构佛塔残件,不知是否弘师塔的一部分。标志性的水帘瀑布,因为巧英水库渠道的拦截,水量大减。本书记载的观瀑楼,虽已不复旧观,我住在靠山的二层木楼上,日观瀑,夜听风,倒也很享受。马蹄岩,已在平整校园时深埋在操场底下,据说就在学校厨房前面那一块。禹余粮石,当地人叫石馒头,当时还随处可见,近年我与研究生柯佳玮一起去,好不容易在山坡上找到了一个,残破的。猪肝石,我班上一位姓周的学生比试眼力,扔石块把它打了下来,目前还能看到根部的一块深红。度师桥,大概在校门的位置吧,到1997年学校动迁,共迎来送往过二十届学生和二十来个教师。锁翠桥,多么形象生动的名字,曾经玲珑的石拱桥已不知去向,我也无缘得见,山嘴也被辟掉了一些,顺势安放了一座小石桥,据说原来的拱桥与山嘴拱卫的造型更像一把锁钥,把山谷紧紧地环抱着,藏风聚气,以致水帘洞一带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外面的山风进不去,里边却能形成小气候,由于热力作用,地面的气流会往上涌,胡柏藩老师在一次值班时偶然发现,挂在洞口的瀑布好像有钩子往上卷起帘子一样往上方漂洒,引来几个学生观看,持续了大约半分钟时间。当年朱熹有诗云:“一片水帘遮洞口,何人卷得上帘钩。”不知道是否针对此类现象而发。洞顶的潜公台,转过锁翠桥就能望见。再往上,现在梨园一带,曾经有两家住户。民居后面叫小庵,是书中记载的追遁庵的遗址吧?已不可考了。后来在其旧址上建起了农中的牛棚,师生们在学农劳动时还掘到过一些旧时的建筑残件。至于书中记载的摘星庵,虽然登过几回水帘尖,但都没看到山顶上有建筑遗迹。俱往矣,目前水帘庵已不见地面建筑,“一片长垂今与古,半山犹听水兼风”,只有潜公台下的水帘,吟唱还在继续,尽管音量与气势稍逊往日。
在水帘庵工作一年以后,我奉调到长诏农中,不过人们照例不用上面给定的名称,而管它叫香炉岩,因为校舍就建在一个叫香炉岩的山坡上,那上面的山头,因为形似用于祭祀的香炉而得名。虽然从一个自行车骑不到的地方调到一个两条腿走不到的地方,颇多不便,可是天天在北窗下欣赏对面天姥山的云卷云舒,心情大好。没入水库下面的这一片,曾经是新昌比较富庶的溪路村落,五代以后定居新昌的石氏家族依水而居,从北宋以来就成为浙东望族,其后嗣每以“石二芝麻官”矜夸。在水库移民之前,溪东真君殿曾经是远近数十里的市集和民俗活动中心,胡卜大旗、东庄大炮、西河花灯、后梁板凳、黄坛三川大旗……,都是其中的保留节目。我在家访时,乡民口中还流传着“有囡不嫁山背等”“十里黄泥岗,廿岁小伙走黄胖”之类的民谚,反衬着溪路的便利与殷实。
后来才知道,水库最宽处的水底下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艳称的沃洲,也是道教的一个福地,因为沃洲山在支遁养马坡到目前水库大坝处往西北拐了个弯,形成了狭窄的山口,挡住了寒冷的西北风;从上游天台山石桥迤逦而来的溪流滋润着沃洲山、天姥山之间的谷地,沃洲因而气候宜人,水土肥沃,溪流两岸的成片良田特别适宜耕种。这个温润秀美的地方引来过晋唐文人,或静修,或放歌,如朱放“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溪边”,刘长卿“禅客无心杖锡还,沃洲深处草堂闲”,于是,在山川形胜外,沃洲也曾经是一方文化高地。
高峡出平湖以后,同样没入水底的还有本书提到的题字岩、玉几、石封门等景点以及桑园、焦坑、十字路、溪东、溪西等村落。海拔118米的放鹤峰,当地人称金刚山,水位低时,还会偶尔露峥嵘。从金刚山往百果园的山岭,就是支遁“买山而隐”的沃洲小岭,这小岭,后来被支遁的大名代替了,叫支遁岭。支遁岭的脚下,曾经有一座破落的寺院,它祖上曾经阔过,那就是白居易撰写题记的沃洲山禅院。禅院后来改称了真封寺,《嘉泰会稽志》八卷已云“旧名真封寺,不知其始”。北宋治平年三年(1066)又改称真觉寺,直到沉入水底,这个名称一直未改。往南,山坡上有一座真君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是这一片库区唯一能够保留的老建筑,这个所在据传是石真人自己选定的,传说中,那奇怪的红石头神奇地来到真觉寺,被寺僧用作顶门石,发现它有灵性后,村民们背它到蝴蝶山(今息坑村炉田禅寺一带),希望帮着看护庄稼,然后灵石自己连夜跑到了这里。今天看来,还真有先见之明啊。民国《新昌县志》卷五载:“沃洲山殿宇巍峨,神灵赫濯,秉香执烛者络绎不绝,朔望愈盛,为新邑之冠。”我走访过新昌7座真君殿,原似各有所供,如沃洲山真君殿,在万历《新昌县志》中叫石真人庙,其来源相传与新昌石氏先人石奕朝有关;三坑真君殿,明朝天启年间还叫五灵山庙……到了清初,这些真君殿似乎一齐新桃换旧符了,全供了抗金名将宗泽。这个现象颇疑与浙东抗清及文字狱有关,鼎革之际,各种不合作势力曾一度活跃在浙东山区、海岛,闻性道以及他这一部《东岇志略》又何尝不是这个多声部的其中一个音符呢?大局底定后,古庙供起了新神,在文字狱高压下,这位矢志抗金的宗泽,可能是坚韧又不乏智慧的乡民们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代言人了。民间这样委婉深微的表达尽管未必会影响大局,但形成了独立于主流的价值判断与历史叙事,甚至会形成小传统与自组织,一个现成的例子是:我在新昌儒岙镇走访时,惊奇地发现两座裘君庙,一在横板桥,一在滕公山,被供在神位上的是晚唐的裘甫,距水帘庵西南10余里的寨岭村,其地名就缘起于他的武装曾经在这里筑寨抵抗官军,《通鉴》称它作“沃洲寨”。在正统史家笔下,这位率众造反的裘甫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但在民间,他可能是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受害者,那些在强权高压下讨日子的民众不仅没有以成败论英雄,反而以这一类非主流反主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心声,耐人寻味。
“沃洲自古少人烟,到者无非避世贤”,这样的非主流在新昌这个浙东山区小县似乎并非孤例,我的以下采访经历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一方山水以及山水中的人文,我把它看成是“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近代版。2019年正月初一,我去新昌、天台、宁海三县交界的几个村落走访,为什么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因为听人介绍说那里几个村落在正月初一时全家聚在一起学说南京话,我想去看个究竟。现属于天台县的银板坑村,全村姓余,说是祖籍在安徽潜山,祖上到南京为官,几代之后,有兄弟二人因故逃离南京,来到这一块新昌的飞地,依赖租种南洲丁氏的山林种植玉米为生。相邻的新昌张宝金村,全村姓汪,宁海蒋家坑村,全村姓储,二者都靠租用南洲丁氏的山林烧炭为生,其来源及到此落脚的时间与银板坑余氏相同。三个村落抱团对外,在这大山深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我采访的银板坑村书记的父亲是来新第七代,目前村里已经有第十代传人了。我问:“现在村里最年长者是来这里的第几代?”村民告诉我说,“第四代在前年过世,去世时92岁”,如此看来,村民中谓洪杨之乱后祖上来到这里的口传大致不错了。我问书记的父亲,是否有正月初一全家聚在一起学说南京话的事,他说不需要学的,相邻的三个村落都说南京话,代代相传,就是新昌女孩子嫁过来,到了这个封闭的地方,自然也会说南京话的。一直到改革开放,村民们有去天台大同、甚至更远的宁波种菜的,情况才发生变化。眼前几位老年人跟我交谈时,还时不时透出南京口音,因为我在南京做的博士后,所以听着还收获了一份亲切。
回到本书。从沃洲到水帘需要翻越一座山岭,人称黄狗大岭,乍听之下觉得好怪,待后来与沃洲小岭的地名联系起来,发现一大一小,相对并提,小岭与支遁相关,大岭呢,大概与来此拜会竺道潜、支道林的王羲之有关,方言中王、黄不分,时过境迁,王公之义渐隐,于是讹成了黄狗。
比起水帘庵、香炉岩等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沃洲、真觉寺、放鹤峰、题字岩等没入水底,如黄狗大岭这样尚存蛛丝马迹可供考查的古地名已是万幸的了。面对沧桑变化,乡人们小心地呵护着他们的记忆,当年建造环库公路时,特意绕过了石夫人像,后来又在放鹤峰西南侧上方的鹅鼻峰上营建了一个放鹤亭,把何梁浦村新建的傍山寺改名为沃洲山禅院,把使用了几百年的“大市聚”镇名改称作“沃洲”——尽管有点不伦……诚然,这20华里水路,7000亩水域下面,有着悠长悠长的历史,又沉淀着多少家族与个人珍贵的记忆,有幸承蒙这一片灵山秀水的眷顾,我们希望通过整理《东岇志略》,为这一方山水和山水中的人们留下点滴记忆,是为记。
在本书点校整理过程中,我们先后得到章月中、叶钟、唐樟荣、胡柏藩、石玉江、徐金超等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敬、致谢。我尊敬的陈百刚老师特地来信,告诉我“沃洲山水风光及文化沉积为新昌赢得多少名声,历代文人也多为沃洲山水歌吟”,“它滋润过你年轻的生命”,嘱我善成其事,殷殷之情,至感。其中肯定还存在许多问题,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