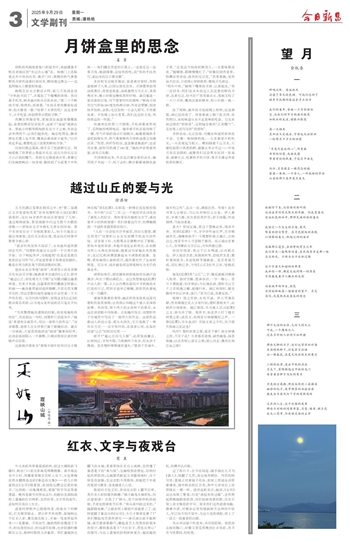姜芽
初秋的风刚染黄巷口的银杏叶,我就攥着手机往老城区的“朱记点心铺”走。玻璃门上还贴着去年中秋的红纸,推开门时,蒸腾的热气裹着鲜肉月饼的油香扑面而来,瞬间漫过鼻尖——这是阿柚从小最爱的味道。
她现在在北方做设计师,前几天发消息说“中秋赶不回了”,末尾加了个瘪嘴的表情。我对着手机笑,转身就问柜台后的朱叔:“要二十个鲜肉月饼,现烤的,别放葱。”朱叔手里的擀面杖没停,抬头瞥我一眼:“给那丫头带的吧?还是老样子,从不吃葱,肉馅得带点肥的才鲜。”
我蹲在烤箱旁等,看面团在高温里慢慢鼓起,金黄的酥皮层层绽开,油星子“滋滋”地渗出来。想起小时候和阿柚挤在这方寸之地,朱叔总会多烤两个,让我们趁热吃。她总吃得急,酥皮掉在衣襟上也不管,嘴角沾着油星子就笑:“以后我走多远,都要吃这口没葱的鲜肉月饼。”
回家时路过菜场,顺手买了把新鲜毛豆。阿柚爱极了我煮的五香盐水毛豆,说北方的毛豆总少点江南的糯气。我把毛豆倒进清水里,看着它们在碗底映出一抹莹绿,像回到了从前某个中秋夜——我们蹲在弄堂的石凳上,一边剥毛豆一边看月亮,她剥得慢,总抢我的吃,说“你的手比我巧,剥出来的豆子都完整”。
煮好的毛豆晾至微凉,装进真空袋时,我特意挑掉了八角,以防压到毛豆壳。月饼要单独用油纸裹好,再放进纸盒,油纸叠得方方正正,角角都对齐,像小时候包糖纸那样仔细。最后塞进一张浅黄的信笺,写下絮絮叨叨的嘱咐:“鲜肉月饼用空气炸锅180度加热两分钟,外皮会更酥,别贪快多加热,会焦;毛豆加热一小会儿即可,不然要发黄。中秋晚上抬头看看,我们这边的月亮,和你那边的一样圆。”
快递寄出的第三天傍晚,手机屏幕突然亮了,是阿柚的视频电话。她举着手机在厨房转了一圈,空气炸锅的指示灯刚跳灭,她戴着隔热手套把抽屉拉开,热气裹着鲜肉月饼的油香立刻漫出来。“你看,我听你的话,没直接进微波炉,也没用水蒸,按你写的调了180度。”她的声音带着笑意,却有点发颤。
月饼刚取出来,外皮还泛着金黄的油光,她用筷子夹起一个,咬下去时,酥皮簌簌地掉在盘子里。“还是这个纯肉的鲜劲儿,一点葱味都没有,”她嚼着,眼睛慢慢红了,“好像回到弄堂里,你蹲在我旁边,抢我的毛豆吃。”我看着她,突然说不出话,只觉得心里软软的,像被月光浸过。
“明年中秋,”她咽下嘴里的月饼,认真地说,“我一定回来,咱们还来朱叔这儿买没葱的鲜肉月饼,还煮毛豆,好不好?”我笑着点头,看她又咬了一大口月饼,嘴角沾着的酥皮,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挂了视频,窗外的月亮刚爬上树梢,还没满圆,却已经很亮了。我看着桌上剩下的月饼,突然明白,有些味道从来不是简单的吃食。它是朱叔记得的“别放葱”,是阿柚念着的“江南糯气”,是信笺上没写完的“我想你”。
月饼会凉,毛豆会蔫,可藏在味道里的牵挂不会。它像一根细细的线,一头系着家乡的秋光,一头系着远方的人。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只要咬到那口熟悉的鲜,就像从未分开过——毕竟月亮总会圆的,就像我们总会再坐在同一张桌前,剥着毛豆,吃着热乎的月饼,看月光漫过弄堂的青砖黛瓦。